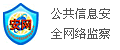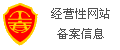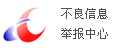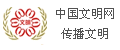“××工作室、××直播、韓國××練習生全球招募活動開始……”每到暑假,這樣的帖子就會在網絡中滿天飛,在大學生的朋友圈里,不少同學也對此摩拳擦掌。選秀一直不是一個新詞,從10年前的《超級女聲》,到現在的各種網絡節目,都受到大學生的追捧。
在95后占領大學校園的今天,選秀活動不再是這一代年輕人“追求夢想”的捷徑,而更多地成為他們尋找自我、展示自我的舞臺。然而,這個尋找自我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95后們特立獨行的行為有時難以讓他人理解,他們天真單純的想法有時會讓心懷惡意的人利用。看來,選秀就是一個“大染缸”。
選秀,是為了“找自己”
然星,是長沙的一名大學生。剛上大學那個暑假,她就去參加了一檔選秀節目。
參賽當天,然星起了一個大早,成為學校門口化妝鋪子的第一個客人。“花了50塊錢,那時候感覺還挺貴的。”背后的化妝師不停說“舞臺妝就是要濃一些”。“于是眼線極濃,還上挑,讓我看起來特別‘狐媚’”。
不僅如此,她還專門為比賽買了一雙13厘米的高跟鞋,還穿上了“看起來很成熟”的紅黑格連衣裙。穿著它們,走在滿是電線的舞臺上,她差點被絆倒,“我覺得導演組一定會喜歡這樣打扮的人”。
“我終于18歲了,我要去參加。成名就像是不高處的果子,我踮踮腳就跟明星一樣了。”然而,那次比賽她止步于長沙的50強。
然星的專業為西班牙語,大三時她去了西班牙交流學習。在那里,她的心態發生了變化。
“我遇上了3個西班牙人組成的樂隊,他們有著不同的職業,但堅持做音樂10年。”然星還記得,有一天,他們一起錄歌時,其中一個成員在場地上跑步。而坐在一旁的其他兩個人則拿起吉他即興給隊友的步伐伴奏。3人越玩越起勁,譜曲作詞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從那個時候起,然星漸漸覺得,因為熱愛帶來的執念并不成熟,而選秀并不是追尋自己愛好和夢想的唯一方式。“把音樂細水長流融入生活可能更本質,成不成為明星就沒那么重要了”。
選秀,風險與光鮮并存
隨著選秀節目的層出不窮,懷揣夢想的95后大學生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展現自我,然而,選秀環境魚龍混雜,有時候“追尋”到的不是一舉成名,而是殘酷社會的深刻教訓。
張寧在四川某大學讀大二,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微信上看到了某房地產公司招募形象大使的選秀活動宣傳。那時候,最吸引她眼球的幾個字是“50萬”——如果在這次選秀中奪冠,將會得到巨額獎金。她自己默默做了設想和規劃:“如果真的可以,20萬元用來出國留學,剩下的給爸爸。”
一開始,張寧一路晉級。然而在某一場比賽中,她突然發現自己身邊“空降”了一批沒有參加過海選的選手。從那時候她開始警惕,“懷疑到最后她們會成為得獎的人”。
而在這個過程中,張寧也感到了疲倦:學業和考試需要完成,參加比賽時間倉促;最重要的是,她越來越覺得“自己其實沒有那么喜歡把自己展示出來。”她依照比賽規定發起親友給自己網絡投票,這讓她覺得“真的很丟臉”。
然而,她最掛念的50萬元也出了問題:按規定,積分隨著票數增長呈正比增長。但是她卻發現自己的積分隨著票數增加在不斷減少。比賽過程中有一個自稱培訓公司以及房地產公司組委會的人提出想要“簽她”。張寧便一直向此人索要合同。
復賽時她見到了“合同”,講述的大體意思是要求選手得獎后假裝拿到了獎金,但實際是公司只是會在日后給選手發工資,而不會得到獎金。第二天,她收到了要“簽她”的人的微信,說“比賽到此為止了”。
選秀,不是“嘩眾取寵”
對于95后從“前輩”那里繼承下來的選秀熱,不少選秀節目工作人員及觀眾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在“展示自我”的路上越走越遠,不僅快要忘了自己的初衷,也快要突破審美和邏輯的底線。
對于大學生參加選秀節目的心態,知名網絡節目《奇葩說》的工作人員何蕓認為,有些大學生可能就是想玩一玩,有些是覺得自己很有個性希望展示自己,有些就是想紅。和他們的“前輩”比起來,何蕓認為95后更加有活力、有想法,更“激進”,更“奇葩”。
作為一個90后,何蕓對于這些“小朋友”的一些行為同樣表示“不能理解”。“我看到的這些報名的選手,很多比較open,言行舉止比較外放。有可能是為了迎合節目取向故意這樣”。
然而,善于表現自己走到了極端就會讓人感到“不適”。何蕓說,有時候會覺得他們有些嘩眾取寵。“他們中有些剛成年,不是很成熟,太急于表現自己了。有一個選手,認為節目需要大膽敢說的人,就故意表現得很夸張,出口成‘臟’,還講黃段子,但在‘見過大世面’的導演們看來,覺得不是很舒服”。
何蕓坦言,從節目方角度來講,肯定希望95后參加節目。“畢竟他們的思維代表最年輕的一代,他們特別活躍,特別青春,能帶來很多有趣的東西。”但是,節目不僅要看表現力和奇葩的個性,還要考查選手的邏輯能力和語言能力。
“我們也在調整一些考核標準,希望他們有自己的個性特征。”何蕓說,對于參與選秀的95后來說,展現個性是好事,但不能流于表面,顯得太急功近利。